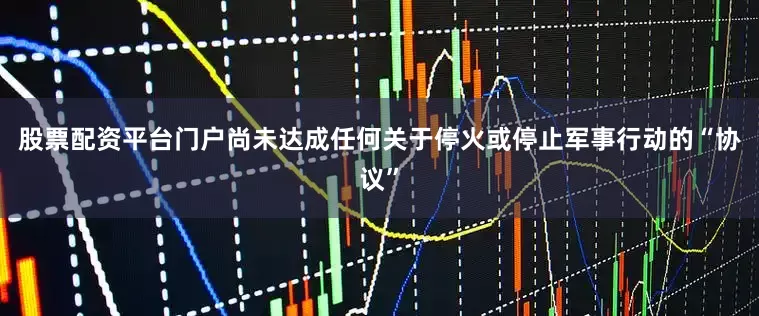《——【·前言·】——》
宋朝皇帝说话不喊“朕”,身上不穿黄色龙袍,自称“官家”,穿红袍上朝。这种“不像皇帝”的作风让很多人误以为他们性格软弱、朝政温吞。事实并不简单。朱门黄瓦不代表实权,称呼和颜色的选择背后,是赵宋皇权对制度、文化和合法性的深度调整。这一切,从赵匡胤穿黄袍登基开始说起。
从黄袍加身,到避黄如火赵匡胤出现在历史舞台,是靠兵变起家。陈桥驿“黄袍加身”那一刻,不仅改写五代十国的剧本,也带来一个微妙的身份焦虑。他不是正统王朝的继位者,也不是士族共推的共主,而是靠部下推举、兵变上台。即便登基成功,合法性的问题始终挥之不去。
展开剩余90%皇帝一旦不靠血统或正统继承上位,就得在其他方面下功夫。赵匡胤选择的是“降低皇帝的神圣感”,拉近与文臣之间的关系,同时淡化“皇权即神权”的传统说法。他穿过一次黄袍就没再穿,是有深意的。这不是忌讳颜色,而是要划清自己与前朝残暴皇权的界限。
宋朝建立后,赵匡胤开始有意识地给皇权贴上一个“新标签”——理性、务实、亲民。黄袍金线是大唐、后周时代皇帝的标配,不但象征天子身份,还代表至高无上的威严。赵匡胤不继续使用,是为了让赵宋不那么像旧朝残余。他不是把自己看得低,而是故意放低皇帝架子,增强“可控性”。
这并不等于他放弃权力,相反,这样的设计更稳固。宋代皇帝不穿黄袍,转而改穿朱红色朝服,正是这种平衡下的产物。红色属火,按五行推演,赵宋奉“火德王朝”,用朱色自居,也合理论框。不是不讲排场,是排场换了思路。
不仅衣着在变,连“皇帝”两个字的表达也开始绕弯。唐朝皇帝满口“朕”,高高在上,赵匡胤却把自己称作“官家”,一来好听,二来不扎耳。百姓听见“官家”二字不会感觉陌生,也不会觉得遥远,这种自称在五代时期就有人用,但赵匡胤把它官方化了,从此变成宋朝皇帝的标配称呼。
“官家”听起来像地方豪绅、家族家长的叫法,少了些神圣感,多了些世俗感。这种处理方式不仅让臣民感到舒服,还方便皇帝插手朝政。宋代皇帝喜欢亲政,常常直接批奏,动不动就出现在议政前线。官家不是装谦虚,是制度需要的表达方式。
穿黄袍是旧传统,穿红袍才是宋人逻辑。自称“朕”是高高在上的代名词,自称“官家”是给皇权加了一层文治糖衣。赵匡胤之后,赵光义、赵恒、赵祯都继续这个设定。皇帝不靠天威压人,靠制度和文化维持统治。即便到了宋仁宗、宋神宗时期,连御前奏章和朝廷仪制也严格规定颜色、称呼,统一成一种“赵宋风格”。
这个风格不是懦弱,而是一种“表面平和、实则集中”的权力策略。别人靠震慑,赵家靠亲民;别人用威压,赵家用礼仪。宋朝皇帝不喊“朕”,不穿黄袍,是为了让权力穿上一件看似文弱的外衣,实际上更方便操控。
官家的语言逻辑:称呼背后的政治心机开国之后,赵匡胤在很多方面都留了心眼。光说“官家”这个称呼,不仅流行于朝廷,还传到了民间。史书和笔记记载,百姓说起皇帝,口头常用“咱官家”“咱朝廷”“咱公事”,语气亲切,几无畏惧感。这种语言塑造不是偶然,而是整个宋代政治文化有意经营的结果。
“朕”这个字,象征皇权绝对性。从秦始皇一统六国起,“朕即天子”,是制度核心词汇。赵匡胤拒绝使用“朕”,是在否定“皇帝高于一切”的传统,而不是否定皇帝权力。他想做的是:“皇帝依旧是一家之主,但是一家人说话不必太硬。”从“朕”变成“官家”,就像从冷宫搬到暖阁,听起来不震慑,却照样有权。
宋代文人地位高、士大夫政治参与深,皇帝不能摆脸色压人,得摆理服人。“官家”这个称呼最妙的地方在于,它不显权威,却能协调权威,既能压住场,又不让文臣觉得被冒犯。皇帝不再是“朕以为然”,而是“官家命你去做”,语气轻了,管用一点没少。
宋仁宗时期,这种称呼体系进一步制度化。不止皇帝,连皇后也称自己“官家妾”,妃嫔称“宫官人”,连太监也会说“奉官家圣旨”。“官家”成了官方内部语言体系的核心代称,有时候比“皇上”更有真实感。
文献中多次出现“官家斋居不食”、“官家遣人宣旨”,都不是虚饰,而是对宋代皇权表达方式的真实反映。赵宋皇帝不是不自信,而是太清楚,自己掌握的是制度王朝,而非靠武力维稳。
此外,宋朝还取消了跪拜叩首中的一些繁琐礼节,替换成“朝贺礼”。臣子上朝不用三跪九叩,改为俯身致敬。这套简化礼制,是为了提升政治效率,也是为了凸显“士大夫可以议政”的文化氛围。皇帝退一步,士人上前一步,形成宋代独有的“文治共识”。
从服饰到语言,从礼仪到制度,宋朝皇帝不打“王霸”路线,而打“秩序”牌。这种自称不是弱,而是一种含蓄的强。皇权看似温和,实则精准;看似亲民,实则掌控。宋代的“官家”,并非摆设,而是制度设计里最锋利的软刀子。
黄袍退场,红袍登基:一场礼制的自我克制大多数人印象中的皇帝,一身黄色龙袍、身披绣有五爪金龙的袍服,走哪都自带圣光。这种形象并非虚构,而是从唐代确立至明清延续的传统。但唯独宋朝例外,从赵匡胤到赵构,无一例外穿的是朱红色朝服。为什么黄袍到了宋朝就成了“禁色”?
黄是土德之色,秦朝定天下,奉土德称黄,黄袍因此成为皇权专属。到了汉唐,更强化了黄为天子象征,是“中正之色”,象征“中土天子”,不可他人僭用。赵匡胤也穿过黄袍,但只限于“黄袍加身”的兵变那一晚。之后再未出现大张旗鼓的“龙袍黄服”。
宋朝为何主动舍弃黄袍?首先是意识形态自觉。赵宋政权建立于五代十国之后,一个兵戎割据、礼崩乐坏的混乱时期。赵匡胤上位靠兵变,自知正统不稳。如果继续沿用“黄袍天命”,必然引起士人、文臣对其合法性产生质疑。与其继续强化“天子神权”,不如主动弱化象征,用红色表达政权新意。
红袍制度也展现出宋朝政权的“去神圣化”意图。在五代时期,皇权与宗教相互勾连,皇帝动辄称自己为“真命天子”、“天地之主”。赵匡胤反其道而行之,把皇帝从“神”拉回“人”,让其像一位理政的家主、一位世俗的权责承担者。
在这一制度下,不光是皇帝穿红袍,大臣们的服饰也趋于一致。高官穿深朱,中官穿浅朱,低阶官员穿青或绿,色阶递进,层级分明。这种服制设计不仅节制奢侈,还强化制度感。皇帝不靠金线刺龙来彰显身份,而靠制度内的礼仪与名分获得尊重。
宋真宗时期,朝会服制进一步规范化。每年元旦、冬至、万寿节、登基纪念日等典礼,皇帝皆着“朱衣裳、金带、冕冠”。黄袍只在极少数神宗大礼或祖宗祭祀中象征性披挂,不得随意穿用。即使如此,黄袍也多为祭服而非常服,不具备政治权力意义。
这种主动避黄、强调红色的礼制改革,在宋代持续三百年,未见中断。连南宋偏安时期的赵构,也未借乱世之机重拾黄袍神话,而继续延用“朱服朝政”礼仪,说明这套制度已经成为宋代政权的重要组成部分,不是可变动的工具,而是皇权文化本身的一部分。
更重要的是,这种颜色策略也在政治宣传上起到了积极作用。宋代文人如司马光、欧阳修等反复强调“君子慎终如始”、“君不言色”,将节制、约礼、崇文的理念灌注进国家意识形态。黄袍在他们笔下,成了前朝骄奢亡国的象征,红袍则是宋政新风的表率。
从黄袍到红袍,表面是颜色变化,本质是国家治理逻辑的转向。宋朝不靠天命强权立国,靠的是制度理性与文官共治。服色只是表象,底层逻辑在于:“皇帝是制度的执行者,不是超越制度的神。”穿什么,称什么,讲什么礼节,都是这一治理观念的体现。
“官家”不是谦辞,是软权力的绝对主语官家二字初听温和,但在宋代,是一种制度内置的权威表达。赵匡胤从不轻易使用“朕”,却频频在诏书、奏疏、命令中使用“官家”。这是主动调整语言权力结构,不再倚重神授皇权,而转向行政秩序与理性统治。
语言的变化不是文风,而是权力再分配。秦皇汉武以“朕”自居,旨在强调皇帝为天地代理人,是“吾即国家”的具象化。但赵宋政权建立时,天下未定,士人主政,文臣集团庞大而有影响力。皇帝再自称“朕”,等同于宣示唯我独尊,容易刺激儒生群体的反感。赵匡胤索性主动去神性,用“官家”取而代之,既保留主导权,又获得文化认同。
更重要的是,“官家”二字自带亲切意味。相较“朕”那种冷峻距离感,“官家”像是一位负责家事的当家人,和风细雨、却也一锤定音。士大夫在朝廷奏章中多用“官家圣断”、“官家所命”,彼此交往间隐含尊重而不畏惧。政治交流的氛围轻了,但决策效率没降。这种语言平衡,很大程度上缓和了皇权与文官之间的张力。
“朕”字不绝对排斥,在诏书中偶有出现,但使用频率远低于“官家”。只有在重大国事,如改元、册立、赦免等具有天命象征的仪典中,“朕”才被刻意使用。那是为了维护帝王仪轨,而非日常称谓。赵宋皇帝既掌大权,又乐于在语言上示弱,让“官家”成为制度背后的心理工程。
宫廷内部,“官家”也成为日常称呼。不仅妃嫔口称“官家”,太监、宫女、宦官乃至御医、书吏都如此称呼皇帝。这个词从宫廷传到坊间,民众说“咱家官家如何”,不觉距离,而感亲切。这种语感嵌入了宋代社会结构:皇帝是掌政者,但不是“天神”,而是制度内第一责任人。
有趣的是,“官家”并不等于降低权威。在众多政治场合中,“官家圣断”一出,就是铁令如山。臣子虽然能议政、能驳诏,但从无越权凌驾的前例。这说明,“官家”虽软,却不弱,是权威的新表现方式。
这种称呼系统,还与宋代皇权的“非神化”进程相辅相成。从不称自己“天子”,也不自封“皇祖圣德”,而是更注重“政德”“仁政”“礼法”。宋仁宗时更设“更衣之礼”“减刑之诏”,主张皇帝作为人,要有自制与悔过能力。连皇帝也有人设、有节制、有责任。
整个宋代,“官家”是制度的文化外壳。它不靠恐吓取信,而是靠语言妥协获取合作。这种策略的最大收获,是宋代文官制度的成熟与稳定。哪怕北宋后期政局摇摆,南宋国势飘摇,皇帝始终掌控核心,未出现外戚专权、宦官乱政的局面。称呼是手段,本质是权力风格的精确表达。
发布于:山东省百川资本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
- 上一篇:配资股票交易网站将深刻重塑每个人的命运轨迹
- 下一篇:没有了